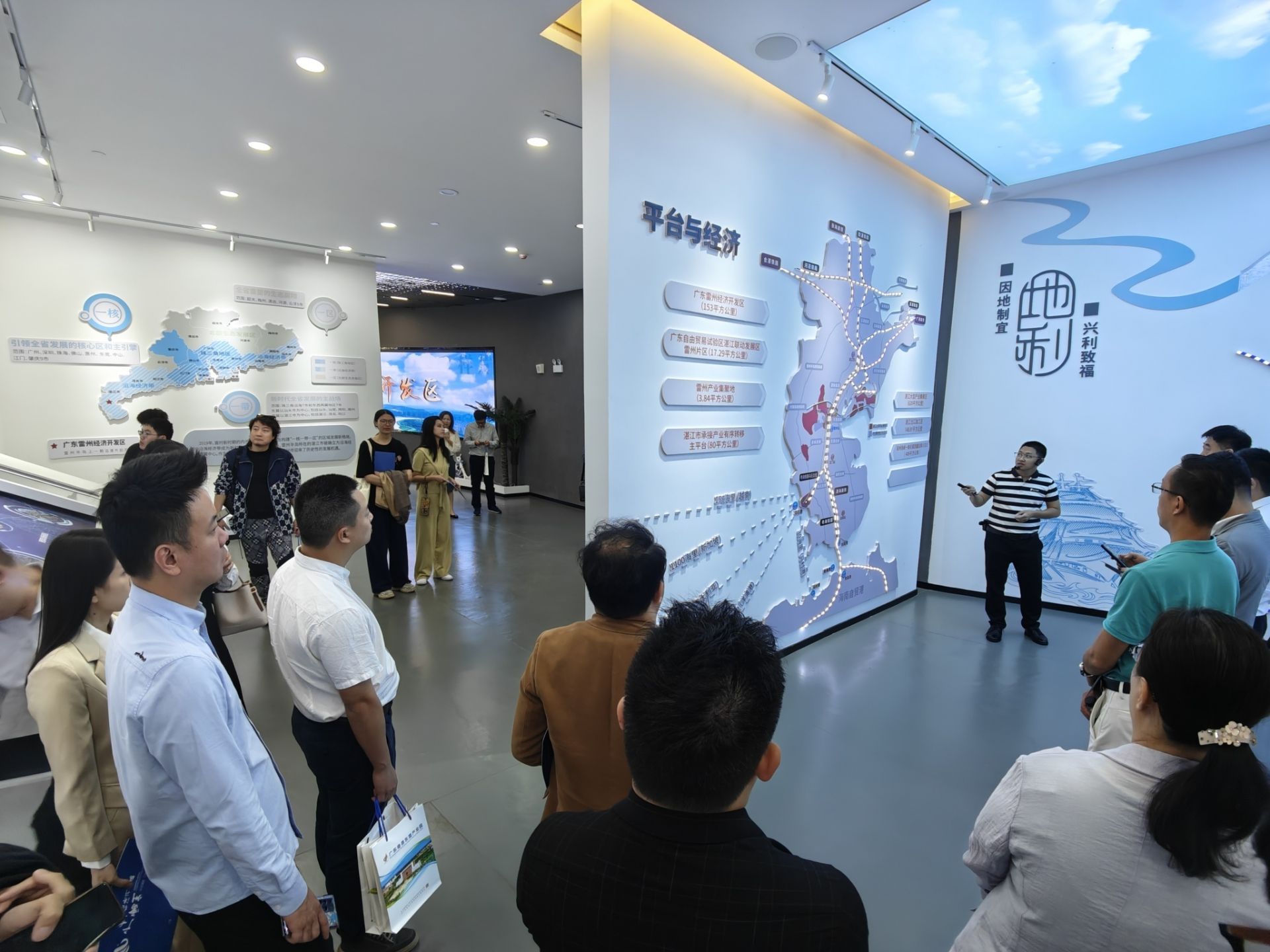冬临鹏城,微寒;翻阅《此心通透即太平》散文集,甚暖。文集中的诸多篇幅,都曾在微信群、朋友圈和报纸杂志阅览过。经廖立新老师精雕细琢、反复打磨后,归纳为“有稼有穑”“山水有灵”“人间冷暖”“书里乾坤”等,共八辑。再读,耳目一新,亦有“温故而知新”之感。
廖立新兼顾多种社会角色,但其第一职业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名副其实的文字工作者。执教三十余年,无论是名家名著、学术论文、报纸刊物,抑或学生作文,廖立新的阅读量是巨大的、丰盛的、多元化的,或者说是全方位的,众生观照,所以“通透”二字,初露端倪。
作者把“前言”命名为《写作是一场一个人的修行》,他在文中写道:“我不得不承认,组织的力量很强大。加入光明区作家协会之后,码字的数量是前半辈子的几十倍。”从行文中不难看出,作协的创作氛围、远人主席的鞭策、文学沙龙中思想的碰撞与交流,都深深地激励着作者,让作者创作热情高涨。文学创作,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。廖立新慢慢地把写作当成一种习惯,博览群书、遍访先贤、笔耕不辍。厚积而薄发,以辽阔的视野、浩瀚的雄姿和淡然的笔触,把农家事、他乡景、桑梓情、书中趣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,如《盛夏晒谷忙》《鹤兮归来》《拼图,还是拼图》等,展现出真挚、丰赡、多样的散文创作成果。
廖立新的另一大爱好:钓鱼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钓者,举足轻重。“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”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“留得五湖明月在,不愁无处下金钩”“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”等等,都是文化与垂钓联姻的结果。垂钓,对多数人而言,难免出现“玩物丧志”的现象,而对于作者却是“钓胜于鱼”。一竿一线一金钩,见心见性见众生。纵情于江河,闲钓于水上,一无所获,抑或满载而归,闲情、雅致、文心、灵感在抛竿与起钓中丰盈。这些与众不同的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条件,频频滋养着廖立新的创作源泉,在作者的笔下时有体现,如《在云髻之巅探测生命的高度》一文中,作者登顶后,在朋友圈写下:登顶何须作证,司马青衫已湿。儒雅内敛的行文,得失随喜的心境。宠辱不惊,把钓者的风范和学者的情怀融会贯通。钓鱼,悦己;写作,耕心。而作者正是在悦己耕心中一步步抵达“通透”“太平”。
对于散文创作者而言,古典文学,尤其古诗词是一个永恒且无穷无尽的话题。作者在诸多散文中引用古诗词恰到好处,如《茅洲河从诗词里流过》,作者在文中写道:“这样的茅洲河才是我所向往的诗意之河,似乎她早已在我的生命里流淌了千百年,以美丽的神话传说为基因,滥觞于遥远的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流过《古诗十九首》,流过唐诗、宋词、元曲……交汇成一首首优美的现代诗行。”而后,引用《高唐赋》《河广》《秋雨叹》《咏凌霄花》,等等。初阅此篇,貌似写人文地理,似乎又有借景抒情的意象。深读细品,作者寓意颇深,把茅洲河放置于古诗词的历史长河中,时空交错,景象万千,将现实的、虚幻的、现代的、历史的多种元素深度融合,这种纵横交错的手法,使得同一景观呈现千变万化的多面性,带给人与众不同的视觉体验和想象空间,文学意象的深度就不言而喻了。
茅洲河是深圳的母亲河,作者对茅洲河的认知、联想和书写,是具体的、真实的、深刻的。无论外景、内心的笔触,都饱含人文情怀和明理哲思。散文集中凡此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的力作较多,如《白花,白花》《光明建筑之美》《一个退休老人的套》等,不一而足。作者以独具匠心的慧眼和极富文学功底的语言,或轻描淡写,或浓墨重彩,于字里行间展露出作者的学识、修为和境界,一步步地激起我深度阅读的欲望。
读“桥里桥外”“地名寻趣”两辑,我更愿意把它们理解为行走的美学、文学与哲学。书名《此心通透即太平》,正是作者在探桥、寻桥、渡桥、读桥中所悟得。
孟子曾说: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。”与廖立新老师相识已有三年,师者、钓者、学者、作者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。拜阅此书,修辞立其诚,文心见其善,其人达者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