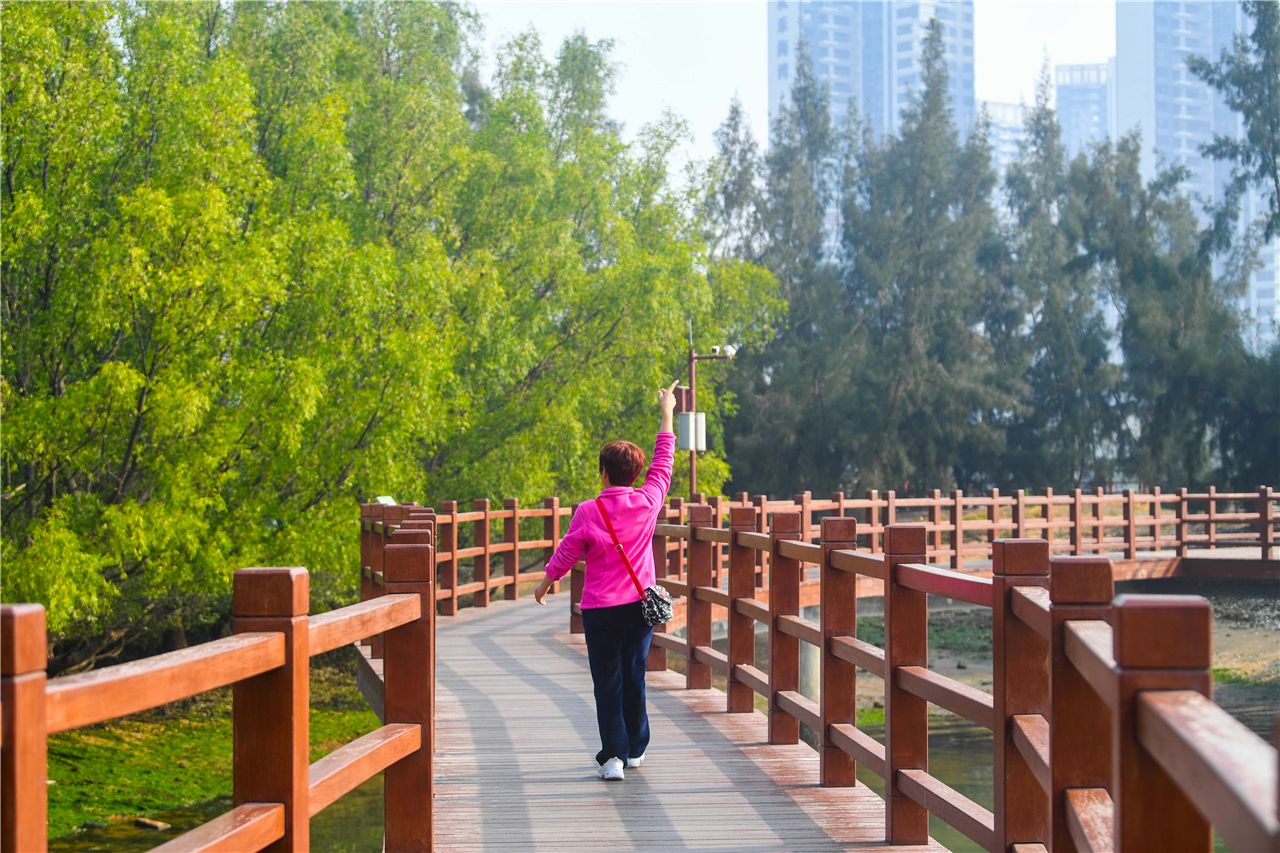家乡的水田,早季种水稻,晚季还是种水稻。
年刚过,母亲就和邻居们商量农事:“你今年还种杂优吗?”
“我今年种丝苗一号,听说丝苗米好吃,我种一年试试。”
“那我也种丝苗一号,你啥时候去买稻种,顺便告诉我,一起去。”
春雨淅淅,田有水了,乡村开始沸腾起来,田野开始沸腾起来,牛叫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,农人肩扛犁耙,赶着牛儿,面带笑容,仿佛一起去赶集。
“早!三叔,你也去犁田?”
“早!五婶,你也去犁田?”
牛儿见面,嘴里发出“哞哞”的叫声,好像也在互相打着招呼。牛儿温顺地套上农具,迈开大步,仿佛一位走上战场的将军。牛儿走过处,大地卷起一垄垄浪花。
插秧了,大人、孩子齐上阵,孩子开始时满腔热情,弓背弯腰,插得似模似样,比写作业还要认真。一会儿,看见水田里一条小鱼,连忙丢掉手中秧苗,跑去捉起鱼来。邻田的孩子听说有鱼,也加入捉鱼大军,一个孩子摔倒田里,变成一个泥人,其他孩子看见好玩,也故意摔倒,田野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大人看见,放下手中秧苗气冲冲追赶过来,孩子看见,像一群春天的燕子,“嗖”一下子飞得四散。
母亲在村里是插秧能手,她插秧快速又整齐。有人插秧为了整齐直行,每插一行,就拉一根绳子对着插;而母亲插秧不用绳子,一只手来回不停,好像穿针引线,插下的秧苗,横看一条线,直看一条线,好像在田字本上的生字。
插下禾苗,春风一吹,开花了,结米了,变黄了,一颗颗饱满的稻谷抱在一起,沉甸甸的,像一团团金子。
母亲说,今年又是大丰收。
是呀,自从领到自留地,我家年年都是大丰收。家里的大缸装满了,谷仓装满了,可是母亲舍不得卖掉一斤粮食。
如果谁家的水稻管理不善,或被虫害,或不及时施肥、除草,或不及时排水、放水,水稻歉收了,成了母亲教育我们的教材:你看,某某人家这么懒,种下稻谷不管理……
每到稻谷收获季节,学校也开始放农忙假。家里有年轻人在外地做工的,父母都要提前打电话通知让他们回来割稻,仿佛家里有一场重大的盛宴,路程再远,路费再贵,也要回来参加。
割稻前几天,母亲天天去巡田,母亲说,水稻收割,要把握黄金时机,割早,稻谷还没有熟透,影响产量;割迟,熟透的稻谷会掉落,也影响产量;还要看天气,如果有台风暴雨,宁愿差一点没熟透,也要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把粮食抢收回家。
父亲在代销店工作,加上身体不好,农事帮不上忙。割稻那天,母亲三点钟就起床煮早餐,然后喂猪、喂鸡,再叫醒我们吃早餐。母亲常说,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
割稻,母亲像一台收割机,伴随着“刷刷”的割稻声,只见一片片稻苗倒下。我和弟妹也不甘落后,一手抓住稻秆,一手握着镰刀,双手不停地挥动。
如今,母亲已经年过八旬,她还不愿意放下农活。我不让她干,她说,我从几岁就开始耕田掘地,耕了一辈子田,土地是我的亲人,是我的恩人,是我的母亲。每天到地里看看,我就感到亲切,感到温暖,感到舒心。只要我还能走动,还有一口气,我就离不开我的亲人,离不开我的恩人,离不开我的母亲。
望着满头白发的母亲,我忽然觉得,母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,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,你要她离开土地,不是要她的命吗?这时,我想到艾青的一句诗来形容母亲对土地的热爱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