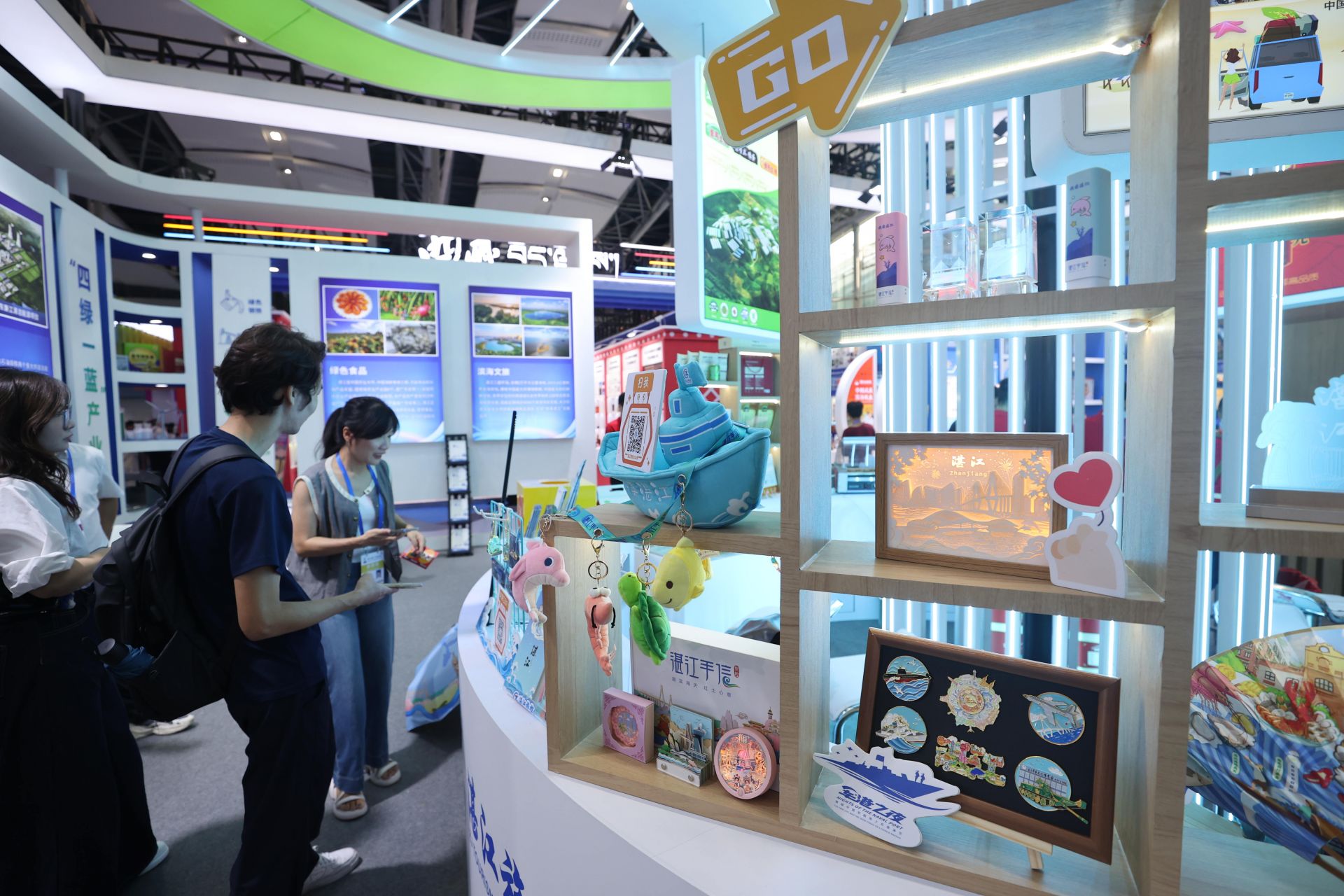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七月中,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处暑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,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。处暑一到,天就变了样,中午空气中还浮着热气,可一早一晚的风,已有微微的凉意。
处暑时节,讲究吃些清热、养阴的食物。鸭子,正是这时候润燥的好东西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鸭肉能“填骨髓、长肌肉、生津血、补五脏”,鸭肉性凉,可以滋阴养胃。秋季可适当多吃鸭子,处暑时节的鸭子最养人。
每年处暑,父亲总会提前一天把养在塘边的水鸭捉回来。那鸭子肥得很,扑棱着翅膀差点挣脱父亲的手。他把鸭子按在石板上,拿起刀麻利地处理干净,热水烫过的鸭毛一拔就掉。“这鸭子养了一年多,肉紧实,炖出来的汤肯定香。”父亲一边收拾一边说,我蹲在旁边看,闻着淡淡的鸭腥味,心里却盼着能快点喝上鸭汤。
母亲在厨房忙个不停,她把剁好的鸭肉放进水里焯,浮沫漂起来就赶紧撇掉,捞出来的鸭肉看着白白嫩嫩的,倒进砂锅里。又从柜子里拿出个小纸包,里面是晒干的陈皮,母亲掰了几块放进锅里,又丢进去几片生姜,“加上这些,去去腥味,还能把湿气赶跑,秋天喝最是舒坦。”
灶膛里的柴火越烧越旺,母亲添了根木柴,火苗窜起来舔着锅底。砂锅盖子盖得严严实实,可没过多久,香味就从缝里钻了出来。一开始是淡淡的姜味,后来就变成浓浓的肉香,混着陈皮的清苦,闻着就让人咽口水。我总忍不住跑到厨房门口张望,母亲见了就笑:“急什么,还得炖够时辰,鸭肉才烂乎,汤才醇厚。”
母亲终于掀开了砂锅盖子。热气“腾”地冒出来,把她的头发都熏得有点乱。她先舀了满满一碗,小心地端到奶奶面前:“趁热喝,补补身子。”奶奶接过碗,用勺子慢慢舀着喝,喝完一口说:“这汤炖得真不错,火候到了。”
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,父亲拿起筷子夹了块鸭腿放到我碗里:“阿女,快吃,给你留的。”我咬了一大口,鸭肉炖得烂烂的,一嚼就化,鲜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,汤汁顺着下巴往下滴。母亲递给我一张纸巾: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屋里满是汤的香味和说话声。
晚饭后,母亲又端出个小砂锅,揭开盖,清亮的糖水里沉着几块炖得透亮的雪梨块,饱满的梨肉在糖水中微微颤动,冰糖的甜香混着梨子的清新扑面而来。“处暑燥气升,喝碗冰糖雪梨润润肺。”母亲一边盛一边说。她把第一碗递给奶奶,接着又叮嘱我:“天气渐渐凉了,别再去河里摸鱼抓虾,小心着凉,听见没?”
窗外的风带着新凉吹进来。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值万金。”这诗句忽然就有了重量——万金也买不回那院子里柴火的暖意、父母的身影,和那碗熨帖到心底的鸭汤与雪梨的甜香了。